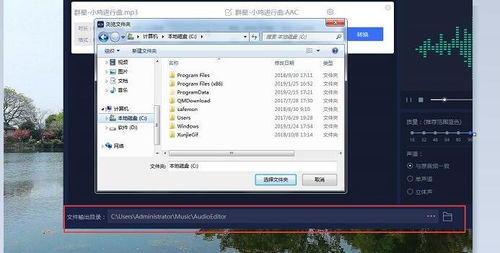文化的面相与儒学的孔洞——读孙晓飞《千年孔子》
自孔子降世以来,孔学或称儒学已经有2500余年的历史,除了极其罕见的几个历史时期外,孔子就一直被神话着。在历史的密林与人语间,孔子被约定俗成的奉为圣贤。连带着孔姓后人也承蒙祖荫恩泽,由被极端的尊崇到赋予实际的特权,享受着孔姓带来的种种无限荣耀。以至于到了宋代,孔子的后世嫡长子长孙被赐授“衍圣公”的世袭封号,绵延千余年,至明初“衍圣公”已经是一品文官要位,到清代“班列文官之首”,还可以在礼仪森严的紫禁城里骑马,在御道上闲庭信步,居住在仅次于皇宫的“天下第一家”的孔府。
象孔氏枝繁叶茂的家族一样,儒家学派也成为历朝历代的“显学”盛术,研究与推崇者如同孔氏家族一样承受着巨大的荣光。如果没有些绝活和新的发现,想有所收获,其实很难。就在这时,一位叫孙晓飞的勇猛者带着他的新书《千年孔子:商周之战、春秋之乱与孔子之变》团结出版社,挟一股清新之气出现在这个声势浩大的队伍中。《千年孔子:商周之战、春秋之乱与孔子之变》孙晓飞?著
《千年孔子》的确有着不凡与非同猩的独特发现,使这部作品成为儒学研究大厦上闪耀的光亮。他找寻到了一条多视角与开放的研究思路,在无数研究资料的基础之上,用独具个性的研究得出了颇有新义的观点。他没有陷入儒学研究的固有泥淖酱缸,而是别开他途,使用了近年西方孔学诸多研究成果,反复捏揉按压,加上中西文化的酵母,孵化出了独具味道的孙氏成果。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借儒学之基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源与流的问题。
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高质量著作,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追索孔子与儒家研究成果的学术研究。他所依据的研究材料,不只限于对国内学界某些收获的理性疏悟,还有对大量现代西方儒学研究成果的吸纳,打开了通往孔子研究的别样通道。如近年来对汉学颇有体悟的法国学者汪德迈,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凯伦·阿姆斯特朗,美国学者倪德卫、夏含夷、康儒博、罗泰、罗莎莉,日本学者白川静、平势隆郞、宫本一夫等等,这些成果是从纯粹研究的客观角度,而不是带有浓重的文化记忆和功利的目的得出的结论,为当下儒学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开辟了不一样的话语视野。
《千年孔子》是把孔子与儒学放在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之下,从对祭祀与占卜,对春秋时代的社会习俗,从神到人的行为规范、文明进步来阐释,即是历史的又是文化的。从认为《论语》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宪章”到判定司马迁对孔子的描述是神话般的“戏仿”,从先秦儒家之源论证到当代社会的“新儒者社群”,使悬空的儒学回到当下的“城市孔学”的终点来,这使他的研究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性。《千年孔子:商周之战、春秋之乱与孔子之变》?孙晓飞著
孙晓飞的研究从微观世界捕捉到了个性与共性的通识,在细节处见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他考据的那些看似琐碎却能还原孔子本相的关键证据,是扎实而有效的。孔子述而不作,本质上的志向并非教书育人,商周是神权社会,神权的本质是皇权。对传统儒学权威的朱熹理论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与反拨,让我们看到了研究的差异化。谁是谁非,谁对谁错,都是角度与深度的问题,不见得是一种高下之别,尊卑之分。
为什么一本专注于儒学的书会从占卜说起?孔子的触须是否可以伸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但这是我们的祖先认识世界体悟现实的源头,也是儒家学说的本源。孔子是坚定的鬼神至上主义者,他不仅相信鬼神存在,而且他所认为的礼所框定的其实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是人与人之间、上与下之间的关系,
按照哲学的判断,世界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构成的,古代的占卜其实研究的是必然性,在纷乱如麻的世界表象背后,那些似乎偶然无序的现象,背后都有某种“天命”和必然走向。古人是完全相信宇宙间就存在着这样的“神奇之手”,我们都在按照“必然律”完成生命的一个自然过程的。因此,占卜与预测便成了某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文化。
把一个人或者一种学问神化容易,恭维、夸大、极端即可,但是被众人推上神坛,却被一个陌生者拽下来,使其回到正常的层面却是难的。其难处是在被神化的过程中,已经培育滋生出了无数的啃食者、寄生者和吸血鬼,那是他们的奶酪蛋糕,谁动了就跟谁玩命,更何况抢食呢?所以,为孙晓飞的横枪立马而捏着一把汗,担心在他头上忽然而至的重击了。
但是,孙晓飞却以自信的学术修为与扎实的阅读亮出了自己的底数,独具慧眼,在密植的儒林深处发掘出了新鲜有味的认知来。

在他的眼里,孔子是“圣人”,不是“神”也不是“仙”,他是介于神仙与人类之间的那样一个“至高”之人,没有超出“人”的范围,但绝不是“凡人”。他在被历史遮蔽的迷雾中,发现并阐明了自己对于史学与孔学的认知。
司马迁《史记》中对孔子身世的“认定”被孙晓飞认为是一种“神的戏仿”。历史可以戏仿吗?历史就是戏仿出来的。文化有真相吗?一切都是虚妄与推导。《论语》里有多少话是孔子的“真言”?儒学的所谓正宗有多少能被历史这位老怪物认可?
因为孔子是“圣”,因此,必然会有“异相”“异能”“异志”。能识麟、具骑射之技,皆为超常之处。
在司马迁的笔下,孔子的出生是母亲颜徵在“感天而生”,也就是以“野合”的形式受孕生子。孔子出生时,父亲叔梁纥70岁,母亲17岁,用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话说“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孙晓飞解释说:“野合,就是在大地之床上受孕。大地之床,可以直接吸纳宇宙的力量,孕育出伟大的婴儿,带来人类之光。”
其实,这皆为“圣人皆有异表”的成见所至,而“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之“为政”也不过是一种创造而已。在孙晓飞看来“司马迁在处理的,并非一个‘实在’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想象中的圣者,?一个仙传人物的‘此在’模型。因此,必须让孔子脱离肉身,成为一个现实社会的超越者,一个能够带领人们走向未来的人。”
我们只能听到热闹的历史杂噪却又寂寥无趣的空间里传来的“呵呵呵”的不置可否的笑声。有没有真相?我们离真相有多远?
孙晓飞所打捞与收获的那些证明与考据是扎实而可信的。他不是坐在书宅里整天以研究孔子为事的“专业学者”,与利禄无关,因而也就不会功利,不会为了讨好而变得乖巧、平庸。
如果我们把孙晓飞和马伯庸两位都出身于赤峰的作家放在一起谈的话,“亦庄亦谐”即可将两个人不同的历史叙事态度说明了。马伯庸的“谐”与孙晓飞的“庄”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照,孙晓飞与马伯庸的年龄差异所映照的时代特征就相当明确了。
因为怀抱还原孔子真面貌的历史责任,他的“庄”显得很沉重,而马伯庸的“谐”却颇讨喜。他需正反两面看,两面读,他得找到那些可疑的地方,打捞那些被人咀嚼过,却没有被有效吸吮干净之处,翻找出可靠的证据,他得“一本正经”。
晓飞试图在做一次文化修补,用自己的储存粘贴那些破损溃烂之处,这个工作做得很吃力,因为他面对着的不只是那些孔洞和破损,更要面对那些啃噬者的威吓与谩骂,以及那些恶狠狠的怒目。
这样的修补就一定会让这个肌体好看起来吗?他的打捞与捕获就是正途吗?
作者简介:

张志强,国防大学教授,鲁迅文学奖评委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